“卡脖子”、关税战,企业越艰难,越要与祖国同频共振
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科技发展和国际合作中屡次遭遇美国的技术封锁与制裁。但奋起反击的中国企业,在很多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时至2025年,中美关税战全面升级,经济对抗从贸易领域蔓延至金融、科技与地缘政治。这场博弈不仅重塑了两国经济格局,更对全球产业链、通胀体系及治理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未来,中国企业何去何从?在日前由山东省国家安全厅主办的“新时代 新科技 新安全”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暨科技安全主题活动——“五盾”讲堂·曲阜站上,一场以“与祖国同频共振是最大的商道”为主题的企业家圆桌对话对此进行了深刻探讨。
本次圆桌对话的主持人为润泽园教育核心讲师郭红波,嘉宾包括金蝶国际软件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徐少春;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增太;海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贾少谦。

以下为圆桌对话的实录(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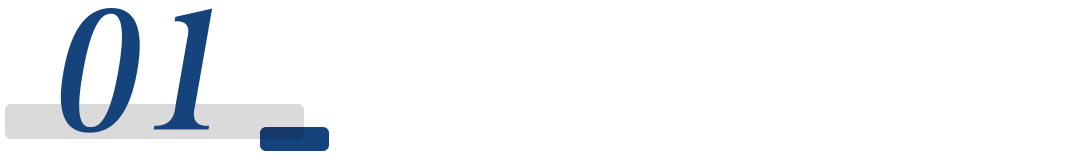
郭红波: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的64项关键技术,2003-2023年均由美国领先,但未来5年或由中国领先。
中国国务院的数据则显示,在35项关键的“卡脖子”技术上,中国有33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关于“卡脖子”工程,三位董事长的内心有怎样的触动?
徐少春:我有两个关键词:特别自豪、特别自信。
国务院提到的取得突破性进展的33项“卡脖子”技术中,有一项是由金蝶在2000年突破的——操作系统数据库。
2000年以前,在操作系统数据库软件上,华为的供应商是Oracle公司。但那一年,在美国的打压下,Oracle不再服务华为。由此,金蝶得以跟华为合作,把华为用了多年的全球人力资源系统进行了国产化替代。
到如今,我们已经替换了300多家大型企业的ERP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一种集成了企业内部各种资源信息以实现对企业各项业务活动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和优化的管理信息系统)。可以说,在高端ERP系统领域,金蝶已完全实现国产化替代。
我的自豪,不仅来自金蝶,更来自行业和国家。通过这几年各行各业的技术攻关,我们有自信。因为我们不仅可以做到科技的安全,还可以做到科技的引领。
廖增太:中国的化工新材料在经济、国防、军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被外国“卡脖子”的材料中,约有70%是化工新材料。
过去几十年,大家主要做大宗化学品、大宗材料。化工新材料属于小众材料,市场规模小、营利性不高、从业者很少。这导致2015年之前,中国很多化工新材料是被卡住的。
化工新材料被“卡脖子”,也与整个产业链有关。拿光刻胶来说,市面上有几十种光刻胶产品,每个光刻胶有几十种原材料。
大家普遍看到光刻胶被“卡脖子”,却鲜少看到原材料被“卡脖子”。只有基础原材料不被“卡脖子”,光刻胶才能不被“卡脖子”。
化工的产业链很长,化工产业链的安全非常重要。没有产业链的安全,化工新材料这个高端产业要实现自主可控基本不可能。未来,我们还要在实现化工产业链的安全上下大力气。
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万华化学曾位列中国创新百强排第三。这些年,我们化工新材料方面创造了大量的新技术。
中国过去几十年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和长期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与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密不可分。只要中国人敢想敢干,只争朝夕、锲而不舍,在创新方面没有不可能的事。
贾少谦:20年前,中国有100多家电视机厂,一年生产约8700万台电视机,却没有一台电视机使用中国自己的芯片,全部来自于进口。
这是因为中国入世(WTO)后,讲究全球化社会大分工。中国做低端制造,高端的器件、芯片来自于美欧、日韩,那个时候中国对“卡脖子”的话题并不敏感。
当美国把中国的供应链切断后,中国才意识到国产化替代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而海信,早在2000年就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芯片设计中心,历经五年的技术创新,通过50多名设计人员日夜奋战,把电视机芯片做出来了。
2005年,海信推出了中国电视机行业第一块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并产业化。此后,中国电视机行业芯片的价格比过去降低了70%。
这说明:当一家企业的关键部件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带动的不仅是其自身的发展,更是所在行业和产业的巨大变化。只有掌握国产化的能力,企业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当中取得优势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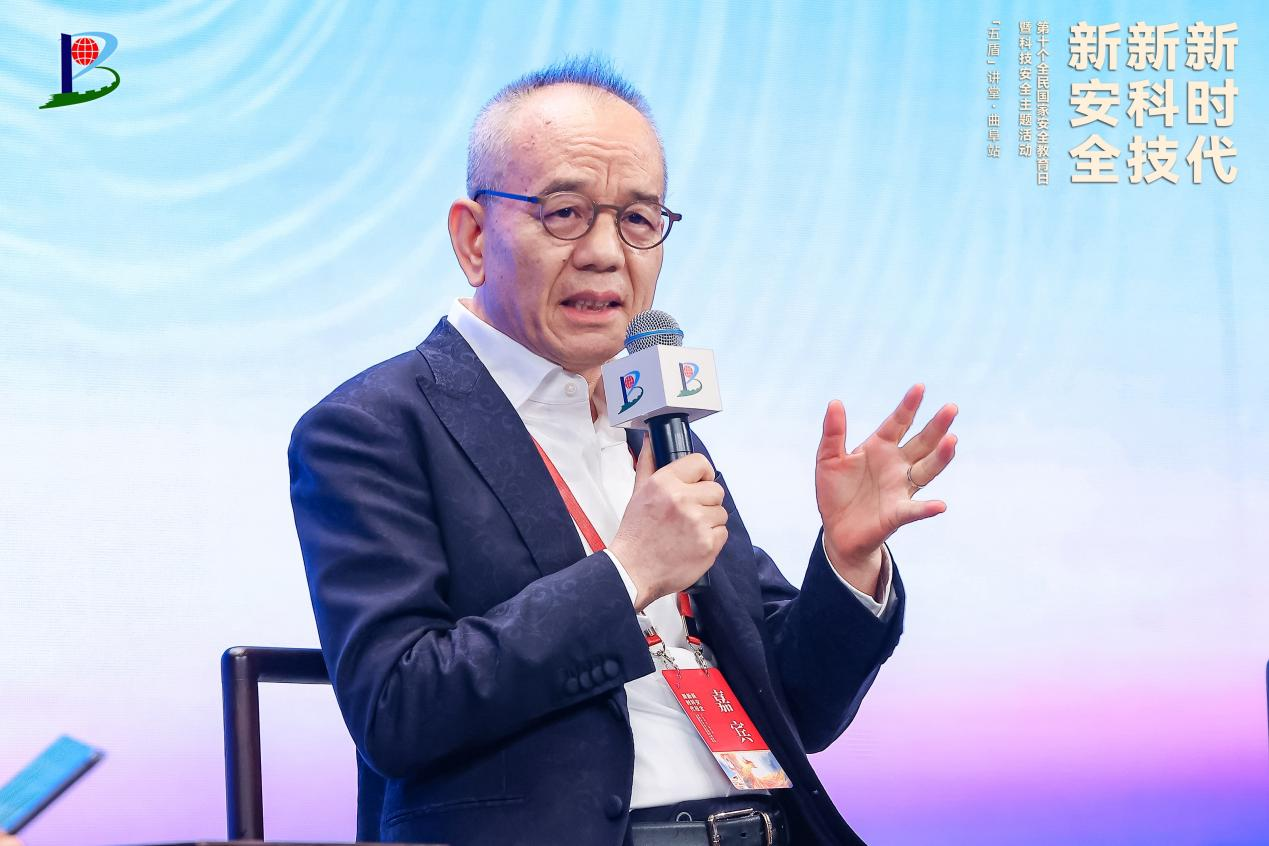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徐少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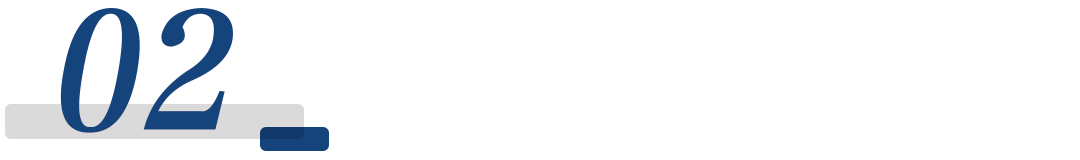
中美关税战:艰难时期,塑造强者
郭红波:2025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挥舞关税大棒,挑起贸易争端,关税战呈现“基准关税+对等关税+额外加征”的三重叠加效应,其中中国输美商品综合税率被一路加征,从10%到20%再到54%,随后又飙升至104%、125%。
出于应对策略,中国对美国加征的关税也从34%提到84%再到125%,许多依赖进口软件的企业面临着成本的压力。
作为各个行业的领导者,三位对中美关税战有怎样的观察和思考?
徐少春:过去十多年,特别是国家倡导科技驱动的战略以后,各行各业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了突破。
今年春节前DeepSeek的出现,更是让美国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斯普特尼克”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字,1957年成功发射入轨时,引起美国朝野的惊惶。美国不能理解,为什么经济、科技都落后的苏联竟然在空间竞赛中抢了先)。
来自外面的挑战越大,美国对我们的打压越大,我们越不能放弃内心的这份自信。
有句话说:“艰难时期,塑造强者”。艰难时期,正是我们铸就伟大的时期,正是让各行各业的领军企业跻身世界一流的时期。
贾少谦:成立于1969年的海信集团经过中国发展的各个阶段:
1978年,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此前,中国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1992年,中国启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2002年,中国开始在WTO的规则下运行。
可以说,海信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发展、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亲历者。
这种发展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中国治理、中国制度不断在产生优势。在这一平台之上,海信顺势而为,与时代同行,才取得今天的发展。
如今,中国在工业、企业层面都有非常好的机遇。尽管我们感受到了挑战,而且有些挑战极大,但我们在历史上经历的困难不比今天少。
越是困难的时期,我们越应该保持战略的定力,坚持用长期主义的思想去指引企业的发展。
我想,中国企业一定能够经历这个特殊的转型期,进而向更高、更远、更辉煌的目标前行。
廖增太: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我相信过去几百年来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有如今这样的经历。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首先要在技术突破上自强自立,其次要把内需拉动起来,还要保持更加开放的国家政策。
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大家聚焦突破“卡脖子”技术,举国发挥体制优势,只争朝夕,久久为功。到2035年,“卡脖子”的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基本上都能解决。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增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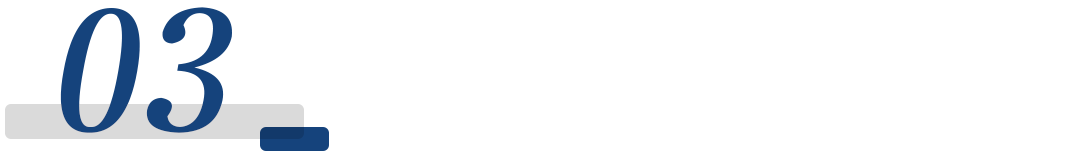
科研型人才培养的关键
郭红波:2021年总书记提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对于如何培养出优秀的科学家、战略科学家,大家有什么样的经验?
徐少春:一是要筛选人才。为什么DeepSeek能成为引领全球的大模型?它背后的团队,不是年龄多大、经验多丰富的人,而是一群好奇心、雄心足够强的年轻人。他们不愿意跟随别人,而是要引领世界。
二是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要让大家觉得,工作不只为养家糊口,更是为了这个行业、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因而在内心产生一种崇高感,并转换为奋斗的内驱力。
我建议,国家要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年轻人心里种下文化自信的种子,以便更好地为实现个人的价值、为时代、为国家努力奋斗。
廖增太:这些年万华在培养人才特别是研发人才上,有三个心得:
1.提供好的文化环境
万华的使命是:“化学让生活更美好”。我们倡导:不只是为了生存而奋斗,更要为民造福、为国分忧、为党奉献,所以万华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能油然而生。
2.提供机会均等的激励机制
万华有三个“没有”:没有裙带关系、没有山头主义、没有利益输送。
从1999年开始,万华出台了自己的技术创新奖励办法,理念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重奖成功”。
拿重奖成功来说,如果科研人员自主开发的新产品成果转化盈利,万华将连续五年按照净利润的15%给其提成;如果科研人员是对于现有工业化装置进行工艺改进,一年内产生的效益按20%—30%提成。
这使得每个员工都会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地考虑如何提效率、降成本,而一旦实现,就能得到奖励。
而高管是不参与奖金分配的。尽管万华的高管大多数是工程师出身,实际贡献很大,但不能参与共享科研成果。
3.提供一流的科研平台
化工是很复杂的产业,需要重视基础研究。
万华有一大批基础研究人才,不光自己搞技术研究,还和大量高校合作搞技术研究。我们还有工艺研究、工程化研究、装机化研究以及产品应用研究。
通过万华的科研平台,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来解决国家的“卡脖子”难题。
贾少谦:“战略科学家”概念的提出和企业创新体系的搭建是一脉相承的。
只有与国家、时代的发展大势一脉相承、同频共振,并在创新之路上不断突破的科学家,才能被称为战略科学家。
我们不仅要崇尚科学、崇尚战略科学家,更要在企业内外共同培养战略企业家。
战略企业家担负的责任,与企业自身以及社会和民众的发展密切相关,需要用创新和奉献精神在民族复兴中体现价值。

(海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贾少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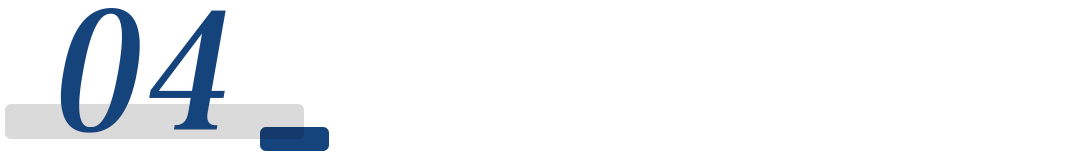
畅想未来:如何践行长期主义?
郭红波: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了很多大国崛起的条件。我想请三位企业家展望未来的画面。到2035年,中国作为科技强国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贾少谦: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可能是黎明前的至暗时刻。
至暗,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一定不只是中国自身的压力,而是全世界共同的压力。
另一方面,这也预示着中国最好的时刻即将到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中国竞争的手段已经穷尽。关税,大概是他们除战争之外最无能也最没有办法的武器。
要追上美国的科技发展,中国还需要较长时间。但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形成,可以从历史的维度来看。
以海信为例,我们从事电子消费产业,先跟美国和欧洲学习,后来跟日本和韩国学习,今天我们跟全世界学习。中国人善于学习,因此在追赶当中实现了局部领域的并跑甚至领跑。
现在是中国走向真正复兴和伟大的关键时期。未来十年,中国打造出强大的科技实力、军事实力、企业竞争实力、品牌实力,实现总书记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对此是充满信心的。
徐少春:2030年,金蝶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企业软件公司;到2035年,我们希望金蝶至少能位列全球前五强。
在软件行业,有两个重要因素:技术和管理。我们“卡脖子”的技术已经突破了,管理模式也要突破。
只有中国软件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最佳实践被外国企业应用,才能彰显我们这个行业真正的强大。所以,我们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管理模式在全球崛起。
过去,我们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卡脖子”。到了2035年,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后,我相信我们不会卡别人的脖子。
到时,这个世界就会实现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而不同、和合共生。我相信这是一定的事情。
郭红波:《道德经》有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有形的产品,咱们已经突破“卡脖子”了。若能在“无”上下功夫,在思想上、在哲学上、在中国文化上、在心上实现引领,才是真正的突围和创新。
未来,我们该如何践行长期主义,把战略科学家、战略企业家的爱国情怀和哲学思想发扬光大?

(润泽园教育核心讲师郭红波)
贾少谦:海信56年的发展历史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创新、国家安全和企业机制的建设密切相关、融为一体。
在未来的发展当中,我们也会借着国家良好的平台和有效的机制,不断地推动技术创新发展的道路。
在总体安全观的指引下,我们也会在建设自己企业的同时,时刻把科技安全放在重要的位置,让科技成为我们未来竞争的长期砝码,助力企业更好地走向辉煌。
廖增太:万华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创新,实现了14项全球首创技术和8000多项发明专利。
未来,万华要更加努力,除了解决国家需要突破的“卡脖子”技术,还要解决人类长期生存和发展问题,比如碳排放。
我相信,通过大家一起努力,中国在科技方面实现自主自立完全没问题。
徐少春:通过过去30多年的创业,金蝶有幸成为一家行业领军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确定了公司永恒的价值观:致良知、走正道、行王道。
我想,在未来30年或者更长时间,只要我们继续秉承这一价值观,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郭红波:我总结一下今天跟三位企业家的对话精华。
1.科技安全是新时代的万里长城,企业家则是夯土筑墙的工匠,我们需要战略科学家,更需要战略企业家。
2.科技是向上向善的,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有这股狠劲以及良好的氛围和平台,我们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一定能脱颖而出。
3.虽然中国面临着被“卡脖子”以及种种国际上的挑战,但艰难时期更能塑造强者。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三位企业家分享科技创新和科技安全的荣耀与责任,谢谢三位!
